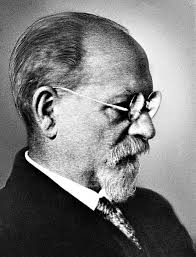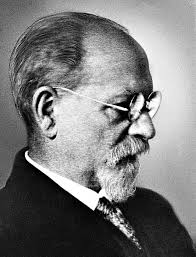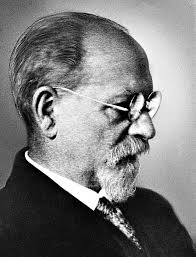毕业了!
终于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
重要瞬间!
致谢
大家都挺喜欢看“后记”或“致谢”部分的,因为它是一个极具公共性事物中显得最为私密的部分。在其中,我们不仅能看出作者的师承关系,也能看到作者思想的变化乃至家庭情况。不知道我下面的文字能否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我的导师孙向晨教授为我们专门开设了论文指导课,从字词句、文章的铺排结构等方面做了细致、深入的讲解。借此,我的论文写作水平有了明显得提升。在博士论文草成之后,孙老师也一字一句的帮我修改,而且论文中很重要的“卢梭”线索,也是孙老师提供给我的,这让我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在复旦,能遇到这样一位老师,可算是人生中的一件大幸事。在我读书的二十几年中,有两位老师对我说过这句话,“如果你是我孩子,我早该揍你了”,向晨老师是其中之一。
学院在设立“副导师制”后,我立即就找了孙小玲教授。她也欣然应允。在读博的前三年,每年除了选孙老师开给研究生的课之外,我还申请做她的TA。在这一过程中,我跟随她读了康德伦理学的主要著作,她每次上课总有一些闪光点。从内容来讲,本篇博士论文的很多有意思的观点受到了孙老师的启发,甚至有些直接就是她的观点。后来,孙老师去南昌大学教书,但我每次有重要的问题都会请教,她也一一耐心回复。如果没有正副两位的导师的指点和鞭策,本论文呈现出现在这样比较像样的样子还是很困难的。“拥有”这两位老师,是我一直引以为豪的事情。希望我日后能变得更练达智慧一些,方能不负他们的苦辛。
还要感谢硕士导师石福祁教授、本科引我入哲学门的胡好教授的多年栽培和提携,他们在我读博后,也时常关心我的学业情况。石老师翻译的赫费教授的书在未出版前供我参引,使得我的论文在某几个关键点上得到了推进。
感谢我的父母。说实话,我很犹豫,不是说不该感谢,而是该怎样。自上大学以来,很多时候我都不在家。为了不让我念书分心,家里有事儿他们通常也不会告诉我。这种恩情是无以为报的。如果说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导师们则赋予了我们“慧命”。有些人偏要继续追问两条“命”之重要性上的差别,在我看来,纯属无聊。因为,我们快乐地接受就好,自己偷着乐就好啊。有人说过一句话还挺好的:我们对生活的理解要深刻,但生活本身却要简单些。
也要感谢前女友和我自己,没有和她在一起的“冲动”,我不会完全地下定决心考取博士。也要感谢我自己,虽然并不优秀,但也一直在坚持自己喜欢的东西。还要感谢那些线下未谋面,但一直无私给予我帮助的师友,如汤沛丰老师、钱一栋老师。至于经常谋面、相互讨论问题,甚至人格彼此渗透的人(如王勤栖,杨根东,姚勇,黄斌,闵奎元等学友),他们被当成了“自己”的延伸。还有几位女性朋友尤其值得提及:李灵婕,姚小琴,张丽芳,常文琦,高婧,吴芸菲。正是她们无私的帮助(提供资料、修改小论文、为我捉急等方面)才使得我的论文变得不那么差劲。当然,还要感谢博士期间参与的研习班以及各种会议上认识的师友(尤其感谢在中山大学第一届“心性现象学”暑期班上认识的师友),也要感谢疫情以来一起读书的小伙伴们,他们促使我更为耐心地倾听他人,更为细致真诚的表达我的想法。
还要感谢丁耘教授、张汝伦教授、张庆熊教授、邓安庆教授、罗亚玲教授,汤铭钧博士、王纬博士、孙宁博士,或是由于参加他们的课程或是与他们之间私下的交流使得我逐渐对学术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既不赋予学术过多也不赋予学术更少的意义,这对我个人来说很重要。还要感谢耿昭华书记、于明志助理和陶香君老师,若没他们的付出,我的学业和找工作可能会变得更加艰难。在上海疫情期间,每每有事,都得烦扰他们。他们每次即时做出反馈也令人感动。
还想说几句。让我对“人”依然抱有希望(或许这个“世界”并非如我之前所设想的那样糟糕)的一个现象是:是那些没有血缘关系(如在没有明显利益纠葛下的师友)、那些素未谋面的人(如只因为一封邮件就给你寄来一本值几百钱的书的人),还会因为“你”做得不够“好”而生气的师友们。在这种现象的背后,除过情感上的关怀和关切之外,其实蕴含着一个简单但却特别为我所重视的道理:对事不对人。这也是本篇博士论文所一再论证的想法。
论文在送审后,盲审专家们给出了一些在我看来非常有益的修改建议,特此致谢。
2022年6月23日
写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