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期间的一点互联网观察
目录
批评与呈现
批评的核心意义是为了指出被批评者有不完善或错误的地方。但批评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有的批评是为了让被批评者变得更好。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之间有特殊的关系或纽带,双方都会感受到善意。有的批评是为了让被批评者出丑甚至失败。如果双方不存在特殊的关系或纽带,恶意就会显露。在许多时候,被批评者有没有错误,是相当明显的。多数时候,批评者有没有恶意,更加明显。如果错误是存在的,而批评是恶意的,那么被批评者应该如何面对?普通个人之间大可以置之不理,敬而远之,而政府则需要动用自己的权力禁止这些批评。
对政府的批评所面临的问题是相当复杂的。有两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人们常常不能很好地区分批评和呈现;第二,内部批评受到外部势力的鼓动,使我们无法有效区分善意的批评和恶意的呈现。
第一,人们常常并不能很好地区分批评和呈现。行动者 A 有一系列可以描述的事实:他的容貌、他的口味、他的身份、他的意图、他的行动、他的行动的后果等等。描述以上任何事实,都是带着特定的目的和价值判断开展的。如果只是展现他的行动的负面后果,就可能并非是就特定议题而言的善意批评,而可能是恶意呈现。
任何的社会实践或现象都有许多的面向,不是所有面向都值得关注,人们总是需要寻找实践或现象的焦点意义,它反映了人们关注的实践重要性。比如,英雄是否有普通人的性情和毛病?当然有,但这些不是我们就特定议题而言所应当关注的焦点,因为它们没有实践重要性。如果只是展现他作为普通人的性情和毛病的一面,就很可能是恶意的呈现。(外部势力的抹黑一贯使用这种伎俩。)对于可能的反驳,恶意呈现的人早就准备好了说辞:“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的确这是事实,但这是不该强调的事实。恶意呈现的迷惑之处在于:通过有意识地筛选事实而达到特定的目的。呈现与批评常常在表面上不易区分,二者都旨在描述一些事实。SI YUE ZHI SHNG 这类视频就是典型的呈现,它静默地挑选所有的负面信息,然后不追加任何的评论和判断。对这条视频的删除愤愤不平的许多人的主要想法恰好就是:它仅仅呈现一些事实,为什么连这样的东西也不能容忍?
政府必须动用权力来禁止这类恶意呈现。政府对人民负有责任,要保持自己的公信力和权威。在公共事件中,善意的大多数人常常是温和地建议甚至保持沉默,但恶意的少数人则上蹿下跳,把自己的一己之见乔装成大众的意见。这就涉及批评政府的第二个复杂问题,外部势力特别善于将恶意呈现伪装成善意的批评。
善意的批评是能够区分问题的不同层次:A 批评 B 时,着眼于 B 的手段而不是 B 的目标和动机,同时二者都明白,A 和 B 有共同的立场和目标。动辄对就将具体的批评转向动机问题,是非常糟糕的批评,甚至很可能是恶意的呈现。
在 3 月底之前,网上对政府的批评的风向急转,让我十分错愕。诸如“幸亏感冒不是这几年新出现的,否则我们现在感冒也得隔离”这样的言论充斥着知乎。这近乎拒绝理性讨论。武汉和西安疫情时,面对政府存在的一些问题,人们的基本立场是,处分渎职和无能的官员,而不是怀疑整个政府的动机。风向转变之后,一拨人的发言想要达到的效果无非是:“你(政府)终于出丑了,你以前所做的事情都是错误的。”
我不是很确定,突然冒出这样一批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倾向于认为这批人混杂了各色人:(1)拿钱办事的汉奸;(2)被汉奸的言论带节奏的憨货;(3)只图一时嘴快的废物;(4)愤世嫉俗者和恨国党。不可能所有人都是 50W。只要你到外网去看看,比如在推特,就能发现一大堆恨国党或恨党党,没有理由认为这些人都是卖国求荣的人。
这种风向很快从知乎蔓延到了微信朋友圈。首先是一大堆的自媒体,起着一个个挑动情绪的标题,暗示政府如何没有良心,而自己如何痛心疾首。然后是一批转发的朋友,常常附上一些表达自己良知共鸣的短评。一些人甚至乐此不疲地表达如下想法:政府是故意搞成这样的,它甚至欢迎瘟疫,这样它就可以拥有更大的强制力量。
政府为什么把“SI YUE ZHI SHENG”之类阴暗的视频给删除了?为什么把“SH 人民已经到了忍耐极限了”这样的文章给禁止了?我不想在这样的问题上辩论什么。我只想直接说出我的结论:它们的恶意呈现和浑水摸鱼的动机是昭然若揭的,任何明智和善意的人都支持将这些东西删除和禁止。
尽管如此,一个巨大的担忧一直存在,怎么才能有良性的批评吗?怎么才能避免,任何批评都会挑动政府的紧张神经?怎么才能避免,对政府的批评导致对政府的彻底否定?以上这些问题是相互联系的。我们一直没有训练公民如何理性地参与公共对话和公共商谈,在所有重大事务上仰赖决策者的明智选择。到目前为止,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运作的,但对于长远的实践而言,这令人担忧。
这么多年的书都白读了?
两个月来,我目睹微信朋友圈一些人乐此不疲地表达良知和明智。这其中尤其以学习法律的为最。(当然,我本身是学法律的,朋友圈中与法学出身的相当多。)他们的表现让我不禁产生一个疑问:这么多年的书真的白读了?如果他们不蠢,那么就一定是我太蠢了。
有一个朋友喜欢在朋友圈抒发心情。他暗示,疫情期间政府的作为让他有了厌世的情绪。他表示,自己早上醒来觉得在这样的世道活下去不如死了算了。他还说,自己每天都感觉被强奸,希望自己不能坐以待毙而有朝一日可以勇敢咬破施暴者的命根子。他还说“一将无能,累死三军,一帅无能,累死国人”。有一个朋友一天转发好几条自媒体的文章,配上自己对学校和政府的愤怒的表达。有一条朋友圈大概是这样的:微信群聊天显示,她的学校要求学生在晚上八点半以后必须回到宿舍,不要在外面逗留:这位朋友就质问辅导员,大意是,“根据行政法的比例原则,行政规定对自由的限制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公共利益,现在学校规定八点半以后不准自由活动就是限制了我的自由,那么学校应当证明这一限制所带来的公共利益是什么?”这真让人忍俊不禁。
这些人中很多研究法律理论的人。可能他们在面对这样的公共事件时,心中想到的就是自由和民主这些玄辩。但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些东西,他们可能既没有深入学好理论,也没有切实观察实践。
唉,一栋说的没错,法学圈子真是智识洼地!
面对这种情况,我都不太敢打开豆瓣。在这里,我关注了一些研究哲学和其他理论的人。一些人开始讨论自己慎重考虑“润”往哪里。让我特别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读书人对时事和政治的判断如此莫名其妙?
下面一条豆瓣知名女拳斗士的一条广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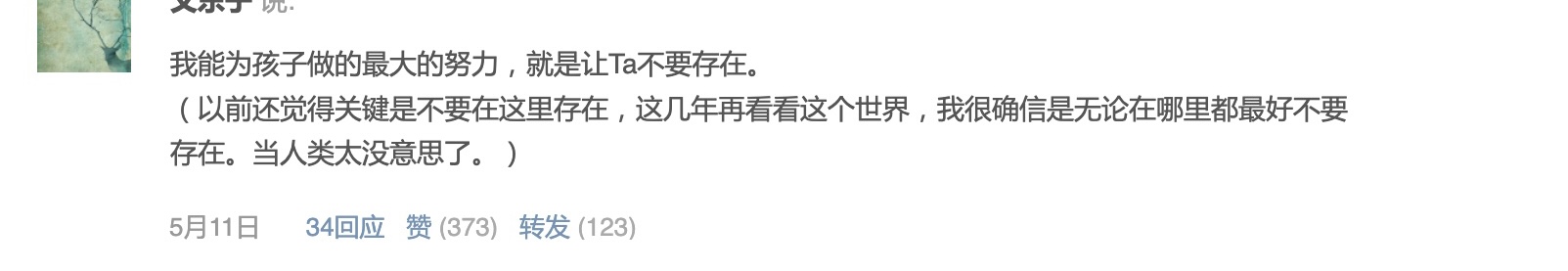
还有一条,我现在找不到了,大意是,一个人说,父亲之前叮嘱在美的他毕业后一定要回国,自从“SH 事件”后,父亲叫他不要回来了。我点开这条评论想看看是否有不同的意见。不少人对这人表达了羡慕之情,有人对其父亲之开明表示赞赏,有人叮嘱这个人一定不要回来,还有人感慨自己没有他的好运气。其中一条评论特别引人注目,得到了 46 个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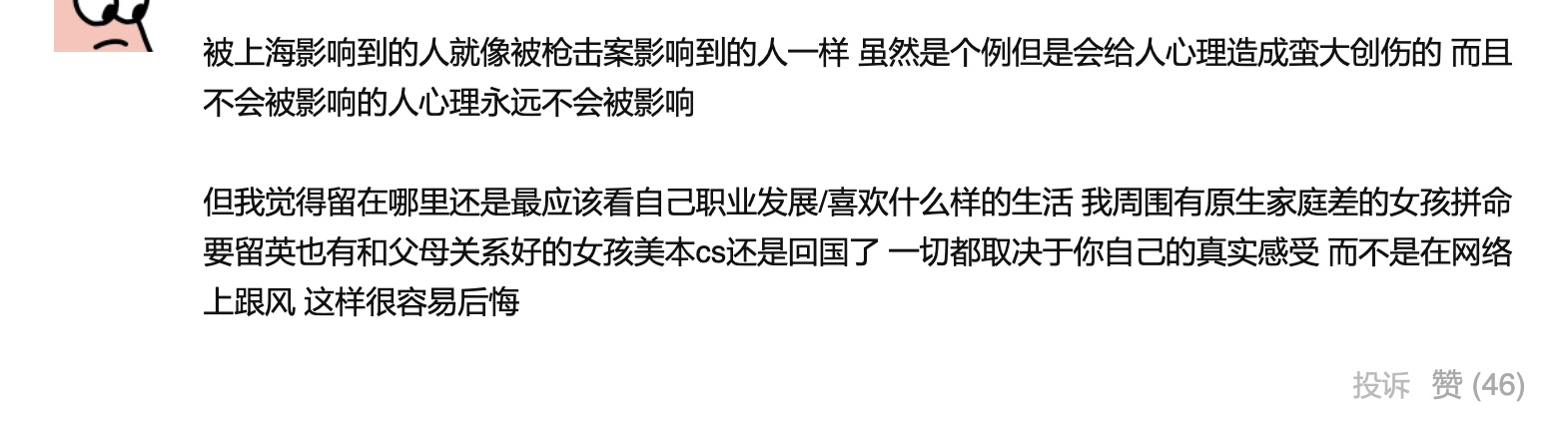
在对这些人评论之前,我先表达自己的情绪:“他妈的,一定不要回来!想滚的赶紧滚!”
这帮人把自己人格的卑下视作高贵。世界都是围绕他们转的!他们的基本逻辑是:“中国现在表现糟糕,所以我要跑到表现优秀的地方。”当然,“如果将来中国建设好了,我还可以再回来。或者,如果其他地方相对变糟了,我会考虑回来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我们不是共同体中的老爷大人,只能被好好地伺候着。如果我们的共同体遇到了困难、出现了错误、遭遇了敌人,我们的一般想法应当是,如何使共同体变得更好。没有这个想法,就没有我们的近代史,就没有那么多先烈抛头颅洒热血。
这种趋利避害的动机,也算人之常情。令人不齿的是,这种沾沾自得顾影自怜的姿态真的令人作呕。或许这些人并非刻意地坏,而仅仅无意地蠢。
国家不是公司。一般而言,国家不好,我们必须建设,公司如果不好,我们可以辞职。当然,只要不卖国求荣,原也无可厚非,但把自己的自私当荣耀,就显得滑稽了。
法治与防疫
我们的法学理论研究出了问题。当然,这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我可以简单说几个要点:
第一,与我们的政治和法律实践相匹配的法律理论的缺乏。马克思主义法学被教条化和政治化,沦为政治献媚的工具。马克思主义法学所包含的许多真理和方法被学生和老师所忽略。可以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根本立场是,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是法律的真正决定因素。若要为法律寻找最终根据,就不是像当代英美法哲学那样寻求什么法律的必然属性,诉诸实践哲学、元伦理学、形而上学,玄谈所谓规范性、合法性、正当性、回应性这类玩意儿。这些绝对远离现实,绝对与政治无涉,绝对只有少数专家能看懂的玩意儿,本来就是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阀内发展的一门精致手艺,本来就是忘记二十世纪哲学的主要教训的倒行逆施的产物。二十世纪哲学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寻求宇宙中无所不在的抽象实体的哲学对于回答世界有什么和怎么样没有任何作用。
第二,目前的政治环境不鼓励法学关注本土的真问题。除非有特殊需要,整个法学群体避免谈论现实,避免研究现实问题。另有特殊需要的人,则把半瓶子醋的西方法学理论用来政治献媚和谋取生计。不研究本土现实问题的人,当然需要特别关心美国的堕胎和种族歧视等现实问题。如果一不留神谈到本土问题,就可能得出,例如“中国法律体系的承认规则是中国法官识别法律规则的惯习”这样的结论。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代英美法哲学已经彻底进化到人畜无害的阶段,放在任何政治制度之中都绝对保证两条效果:第一,没有多少人会真正感兴趣;第二,绝对不会对政治和法律现实产生任何影响。当前英美法哲学的精致讨论,已经流于琐碎乃至鸡零狗碎。在有意无意避免对现实产生影响方面,英美法哲学家们相比其他国家的法哲学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使我想起一栋的一句话,如果文科论文只有几个专家能看懂,也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了。这原本是用来批评国内文科界的,但当代英美法哲学界,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在《当代英美法哲学可能已与法律无关》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讨论。
厌弃马克思主义法学的青年人一头扎进英美法哲学的精致游戏之中,皓首穷经也未必能够搞清楚一两个“理论问题”,不可能有什么时间把目光投向自身所处的现实,即使偶尔环顾周围的环境,所发出的思考也相当青涩。至于其他法哲学,像是当代的自然法学,也有这个趋势(不过我对此不是很熟悉)。至于社会学法学、传统的欧陆法哲学,有许多只是没有经受二十世纪哲学洗礼的哲学古董,压根就没法使人把话说清楚。
第三,本应该在法律理论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越来越被教义学和社科法学边缘化。没有政治哲学和法哲学,对于厘清我们的实践中的道德、政治、法律和强制的关系,是相当不充分的。这个问题现在看来越来越紧迫:面对我们的政治和法律现实,要么钻研无用的英美法哲学以规避现实,要么将马克思主义法学拿来政治献媚。
我们的实践得不到理论的充分支持和更新(update)解释,从长远来有极大的危险,尽管近期看问题并不迫切。这样一个问题,我有机会再继续讨论,下面我将结合一个具体的例子打开一点思路。
在这次疫情之中,不少人高举法治的旗帜。法治一个核心原则是,法律要提前公布,政府的法律决定与提前公布的法律保持一致。法律规范和法律决定存在确切的一一对应的关系,每一个法律决定都有对应的法律规范作为根据;这从来就不只是单纯的理想,因为从来没有在理论上说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稍微思考下就能明白,像这样紧急和特殊的公共卫生事件,法律是相当滞后的,要想每一个法律决定都有法律规范的依据,其困难是相当明显的。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法律理论中至少为法律规范、原则和政策的区分保留位置,考虑政府的法律决定和政策在不那么符合法律规范的情况下,是否得到原则的支持和辩护。任何具体的法律规范都受到某些原则的支持或辩护。在许多情形中,原则反而比具体的法律政策更好地调整和辩护我们的行动。尽管如此,法治原则过于一般化,甚至只是支持和辩护政治和法律决定的诸多原则的一个。至于政策,现在就变得更加重要,因为许多重大紧急所面临的环境是法律规范在其制定时所完全没有的,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必须给予政府充分决断的自由和权力,对这些自由和权力的评估,需要法律规范和原则同时参与其中。一项决定是否合理,需要整体考虑规范、原则和政策等因素,从而作出明智的判断。
我上面提到政策考虑中最重要的目标是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这两个月来,有不少人转发的小视频是反映一些人抗拒防疫政策的。这些视频无不对这样一个问题保持沉默:防疫政策是否要求每一个人的配合?任何一个人脱离管理,都可能造成指数级别的危害。即使是老人也不例外。老人被强行转运,无非是他们拒绝。那么如果因为他们是老人而网开一面,那么人人都可以找到自己不配合的理由。遇到这样的视频,我常常留意评论,看看是否群众在这样的事情犯糊涂。记得一条视频的标题大概是,“就是视频中这些工作人员给政府抹黑的”,下面的一条高赞评论的大意是,“他们什么时候白过?”人们对政治、法律和强制的关系缺乏恰如其分的一般理解,比如,对强制是法律的生命这一点缺乏必要的坦诚。政府的法律是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的,但法律仍然是以强制为支撑的,政府采取强制居然能够激发一些人直接完全否认政府,这是相当值得思考的现象。
研究宪法和行政法的 TONG 教授——此人一直就是一个“公知”,早年在微博一直高举自由民主法治的大旗——前段时间在一篇呼吁防疫要在法治的轨道上开展的文章中说,根据相关法律,防疫是政府的义务,而不是人民的义务。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得有多混蛋?他的基本逻辑就是这三十年来自由主义法学的基本逻辑:
(1)法律的基本功能是限制政府权力保证公民权利。政府是必要的恶,是需要防范的对象。
(2)政府和人民是一组对立面,政府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不是相一致的。
这些说法当然表达了极为珍贵的真理,但也存在相当明显的问题,比如,法律的执行机构既然是政府,而不是人民,那么人民拿什么来让政府用手中的法律约束自己?还有,我们打算将这些真理联系于什么样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或者我们可以问,我们打算将它们联系于什么样的关于道德、政治、法律和强制的更深层理解,乃至于关于公共体的一般事业和人民的共同福祉的最一般理解?
如今疫情肆虐,有人居然主张,防疫只是政府的责任。那么政府防疫是为了什么?防疫是为了避免人口损失太多了,影响自己统治利益吗?有必要刻意在这些根本问题上造成政府和人民的疏离乃至对立吗?对政府动辄恨得牙痒痒有什么意思?先搞清楚自己的立场,你是要建设它还是要推翻它,或者只是想尽情嘲弄。
不区分政治和法律的层次,在任何层面上将政府和人民视为对立面,真的符合我们的现实,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政府和人民的对立仅仅在一个相当有限的层面上,而这一对立必须以在更一般的层面上的统一为背景。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尽管有不如意的地方,但我们政治叙事从来不是把政府描绘成人民需要防范的对象,使政府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如果我们不区分一些层次,那就会有如下的效果:政府做对了是履行了应尽的义务,做错了就立刻成为咬牙切齿的对象。我们不能放任我们的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落入这样的陷阱当中。
我们需要更好的政治法律理论
两个月来,关于法治与防疫的话题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讨论。我在上面已经简单提出了一个现象:要么几乎完全看不到理论研究者的理论在这场身处其中的公共事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由此产生的只有厌弃、愤怒和愤恨的情绪,要么就是将它们的理论硬生生地套用在我们的政治和法律实践上,以至于弄出“防疫只是政府的责任”这种混蛋结论。
我也解释了部分原因。西方现代法学的基本观念源自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法律是人民用来防范政府作恶的,人民是为了更重大和基本的理由才忍受政府这种必要的恶的存在。这个观念是否正确,不是我今天的主题,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至少在我们的政治叙事中,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套用拉兹关于权威的一个论证:法律必然主张权威,为使其名副其实,法律必须要变成什么样的。类似地,我们的政府确实要主张为人民服务,为了使其名副其实,政府必须要变成什么样的。
现在我想提出另外的一部分原因。我们的政府有关传自己与人民、法律与人民的关系的政治叙事,并非不存在任何问题。政府有没有可能完全和人民完全一致?在某些政治层次上,完全可以这么说,而且可以适用于古今中外的任何政府。但在许多政治层次上,必须承认,政府和人民的确是对立的:政府垄断了强制力,必须治理人民,而人民必须一般地服从;政府既需要法律来治理人民,人民也需要法律来约束政府。法治的理念应当在这个层面发挥作用。
由此,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并非在任何层面都贯彻始终地处于同一立场。政府必须真诚地向其人民表达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说,法律的生命在于强制,法律必须要求服从,而强制的背景是政府与人民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整个共同体必须要有一套对强制的辩护或证成,在强制得到辩护或证成的时候,坦率和安全地运用它们,这是良性政治和法律实践的一个必要条件。
官员和学者需要对道德、政治、法律和强制的相互关系有一般的理解。在不同层次上,政府和人民的关系需要不同的刻画。只要我们能够在不同层次正确处理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我们就不会在具体问题上陷入混乱。比如,在紧急事态中,对于政治而言,政府显然是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的重大利益而这样做的,而不是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力,对于法律而言,政府执行政策和法律必须以强制为依托,对于拒不配合的无论任何人采取强制措施,而这并不因而使政府在政治层面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有关强制的正确议题不是质疑政府的意图、目标和性质,而是强制的法律根据和必要限度。否则,就会有人被坏人带了节奏,连政府的意图、目标甚至性质都要怀疑。比如,有人说 SH 政府三番五次上演“狼来了”的把戏,一再说要解封但一再继续封控,言下之意是说,政府诚心耍弄人民,对自己有机会使用强制感到意犹未尽。政府每一次都只是在提出目标和希望,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政策和执行法律,但病毒不会按照政府的目标和希望来活动,当目标未实现,除了继续封控还能做什么?政府在描述强制实践的公共话语中,将政府和人民完全放在同一立场是有问题的,这混淆了政治和法律的不同层次。其问题之一是,如果政策和法律的执行不利,就会遭到极大反弹,波及的就不只是法律,还有政府本身。
在这场防疫中,所暴露的问题实在太多。第一,理论研究者离胜任为我们的政治和法律实践提供支持还差的很远。第二,我们的政府在描述自己与人民的关系的公共话语中,还需要对政治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更恰当的区分,使得官员和国民都能有层次地思考问题,而不是对任何层次的问题都采取“一竿子到底”的思维。我们必须努力避免,在特定的时候,比如在防疫成效显著的时候,政府的威信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在防疫遇到明显困难的时候,政府立即被一些人骂为匪帮。我们太需要细致处理我们的道德、政治、法律和强制的关系的理论了。我们需要认真地和真正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和法律理论,并且在这种理论和学界流行的自由主义政治和法律理论之间建立连接、判断和评价。把马克思主义法学作为政治献媚的工具令人不齿,深研西方政治法律理论的人对自身处于其中的政治法律实践作出的近乎孩童版的判断令人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