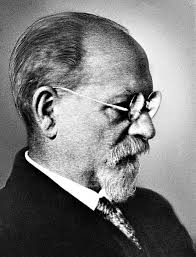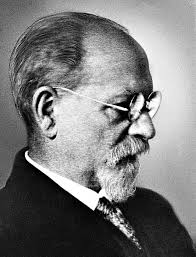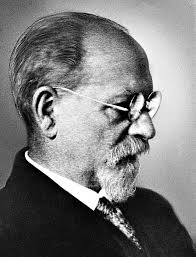书评:布兰特·莱因哈特:对《道德形而上学》的一种辩护:与克里斯托弗·霍恩商榷
布兰特认为,霍恩的做法使得康德哲学回返到了亚里士多德。

克里斯托弗·霍恩展示了一幅内容丰富的康德哲学图画,特别是其法权哲学和“政治哲学”。在精确阐释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非理想性的规范性”和“政治哲学” 论域与康德相关的著作、反思和讲座的切磋中获得了一个新的面向。该研究恰恰呈现了这一点。
霍恩自然知道,在康德那里,按照原著,既不存在一种“非理想的规范性”[1]也不存在一种明显作为统一体的“政治哲学”。关键是,他将自己的标题概念(Titelbegriffe)与作者对立了起来。相反,康德将法权置于《道德形而上学》的标题之下,具体来说,置于“法权论的形而上学始基”(1797年)的标题之下。然而,在霍恩的内容概述中,形而上学这一概念看起来没有位置,甚至形而上学在其书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霍恩构想出了一个非理想的规范性和政治哲学领域,它源于如下的困境(第一章):定言命令完全有理由被刻画为道德性的理想规范;那么,法权能否从锚定在批判哲学中的规范中推导出来呢?有一部分康德研究者赞成该论题,持支持依赖论,另一部分则反对该论题,持非依赖论(尤其是第9页)。按照霍恩的观点,第二种立场是不成立的。因为法权并不是描述性的体系,而是要设定诸多规范。另一方面,把法权和它在政治中的应用从完美无缺的定言命令程序中推导出来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因此,霍恩与依赖论建立起了联系。不过,他进一步通过那些无法从定言命令中获得的规范补充了法权和政治的基础。这样一来,他将两种看起来势不两立的观点结合了起来;他赞成如下这种规范性。它并不是完美无缺地与定言命令的理智基础相关联,即便如此,它也能为实现幸福的法权和义务奠定基础。这种非理想的规范性就是这本书的主旨。
我将分两部分呈上自己的批判性分析。在第一部分,我将试着指明,依赖论和非依赖论区分的前提是不恰当的,因为它耽搁了康德形而上学的理论类型。
康德自己通过无法推导的质料性的内容丰富了定言命令的规范性的形式基础。《法权论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既是一种先天的、同时又是经验性的法权实现的学说,它带有自身的、无法推导的质料上的诸多设定(Setzungen)。在第二部分,按照这种诠释,霍恩刻画为“非理想规范性”概念所带来的问题依然存在:定言命令在其所有有缺陷的实定化的形式中,始终统治着实定法权吗?我们是否并非必须通过一种非理想性的规范来补充理想性的规范或者当涉及我们的基本幸福时,从根本上接替后者?与其说康德,不如说亚里士多德或罗尔斯才是严格的非理想规范性的作者?
I. 康德的法权形而上学
“一般而言,仅仅表示什么是责任的定言命令就是:按照一个同时能够被视为一条普遍法则的准则行动!”(MS,AA,6,225)这是纯粹实践理性的自由法则,它对于自律的理性存在者(不是:理性存在者,RGV, AA 06:26.09u.ö.)而言是构成性的。这是一条为法权和德性(伦理学)施加其义务的道德法则。对于霍恩来讲:只存在一种义务(302u.ö.)。法权和伦理(这种顺序有其必然性)前后一贯地服从于作为立法者并同时自我强制的(Sich-Selbst-Unterworfenen)人的自律原则。自律不同于伦理义务,亦即使得道德法则自身成为行动的目的或动机;它也不同于一般的自由法则,因为后者只是假言地适用于纯然的理性存在者,某种魔鬼民族,因为它已然排除了(解释了),每一个人的自由与其他所有人的自由按照一条法则的一致是最明智的事。在这儿,人们很容易记起来这件事。与之相反,康德将自由的形式与法权的自律关联了起来,并由此人作为人格的身份(status),例如在刑事司法中不允许纯然被视为手段;相反,魔鬼能够遵从一条命令将通奸者施以石刑的法则。他们仅仅具有一种不服从任何道德禁令的工具理性;在康德那里,他们只能是臣民,而不可能是自律的、立法的公民。
在这几个小点上,已经有一种质料性的设定(Setzungen)被引入了。它们无法从纯粹实践理性的最高原则中推导出来,但是它们需要先验哲学。它对于依据人的(unter Menschen)法权实现而言同样是先天必然的[2]。“继《实践理性批判》之后的,应当就是《道德形而上学》这一体系,它认为法权论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和德性论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作为已提交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的一个姊妹篇)[……]”(MS, AA 06:205.02-06)[3]。这一点很关键。KpV为如下一种存在者推送出了一种应然学说,他们既具备纯粹的实践理性,也具备一种抵抗性的感性。与之相反,道德形而上学要运用于理性的存在者;这一点在法权论中意味着:在准先天的自然条件之下,实现法权的理论。首先,属于这一理论的是:在外在(空间)和内在(意向;设定目的)[4]之间的区分基础上,区分出法权和伦理。因此,法权禁令也被当做了伦理学的目的,正如在理论哲学中,外感官的现象同样也是内感官的对象一样;空间之物将在时间序列中得到表象[5]。就外在的东西而言,又一次地被分为了外在的我的和你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自己的身体和对人格的尊敬都被计入了后者。法权是自由法则的领域,对它的遵循是可以外在地强制的,与之相反,伦理学只允许内在的强制——这种区分只有在形而上学中才是可能的。例如,在婚姻法权和亲权中,丈夫、妻子和孩子之间的区分、作为有限的人类居住表面的地球之圆形的境况、自然状态和市民状态之间的区分(“逃离自然状态的法权禁令”,同样伴随着强制)、国家的复数性,所有这些都缺乏体系但却必定是超越经验的。《道德形而上学》是——首要是——中介(Vermittelung)理论,它联结了定言命令的纯粹先天性和在我们世界中的引入的经验的-先天的、质料的、但却并不是推导出来的事件,在其中,道德性应当得以实现[6]。
然后是第二方面:法权之总体并不是从定言命令和“法权概念”中逻辑一致的引出的(MS, AA 06: 247.03),而是从一项补进的“[sc.纯粹的,RB]实践理性的法权公设”(MS, AA 06: 246.04)推导出来的:每一种属己的我的必须通过一种非对称的我的捕获才能成为专属我的;世界赋权(Weltbemächtigung)的公设促成了定言命令和法权学说中行动总体之王国的中介(Vermittelung)。“这个是我的”(ceci est à moi)合法性的法权公设在经验-先天的境况中从头至尾发展出了一种法权实现的元-历史动力学。“不存在外在的我的和你的”,这一论题并不矛盾。然而,正如黑格尔强加给康德的那样,它违背了最初的命令(fiat)[7]的公设。这一公设驳斥了唯心论,这种唯心论在纯粹的观念领域依然是可能的[8]。
第一种领域关联到我们在其中行动的准先天的世界状况,与之相反,公设构成了一种对如下情境的必然的允许,亦即允许单方面的对其他所有人自由的临时限制直到在永久和平中对于你的和我的的最后的、全方面的承认。
因此(于是):法权论依赖于批判哲学和道德哲学(与非依赖论相对立),但也无法从定言命令中推导出法权之经验-先天的材料(与依赖论相对立)。艾宾浩斯为人熟知的非依赖论并没有注意到法权论形而上学的初始根据,其中,康德明确地使用了先验哲学(例如,在理智占有的概念中,MS,AA 06:249.12-13)和道德命令;他的论题在这种简单的文本证据之下垮掉了[9]。与之相反,依赖论阐释遗忘了法权论的形而上学、与之相伴随的经验-先天的诸多设定和无法推导的(纯粹)实践理性的公设。
在对《道德形而上学》有所缺陷的接受的过程中,如黑格尔所主张的学说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影响,亦即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在原则上,这一点始于KrV,也就是1781年;康德1797年推迟了的标题在历史上是最后一个——直到今天,没有人再在其著作的标题中使用形而上学这一过时的概念。形而上学,一种沉迷于掌声的时代精神,由于康德的批判而被清算了。就连康德也看出,形而上学的标题也被视为了“学究式的矫揉造作”,仅就其外貌而言,就已经十分吓人了(AA 23:374.11-16;同样参见,GMS, AA 04:391.34f.)。与往常一样,1797年短时期重现的后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创设的材料和区分,对于GMS和KpV(1788年)必然是先天陌生的。相反,康德1797年引入的形而上学事实上要为一些十分现代的东西负责:在经验的-先天的条件之下,全球性的不断进步的法权实现进程。
因此,在MS中,康德断言,从(尽管)权威性的(machthabenden)定言命令中推导不出他的批判的法权论;通过公设,也就是针他人的非对称的临时的对自由的限制的许可法扩展了概念领域,并且通过自律原则补充了外在自由的法则性的规整(Regulierung):潜在的公民不只是臣民(正如在艾宾浩斯那里),而是人格和自律的立法者。一切在观念性之中。如果人们注意到GMS、KpV和MS之间系统性差异的话, 那么,将会标明,把MS与前两者对立起来的做法是多么危险了。而霍恩总是这么做的,尤其是3.3中论“法权概念的疑难和责任体系”(144)。
两点补充:在这儿人们已经看出,命令准则的普遍化测试不能带来任何东西,而只能将具有感性的理性存在者从道德性的自我关系中转移开(?)。它在寻求规范时是有所帮助的,当我问自己,采纳如下的准则,亦即在我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或者仅仅出于厌世而破坏生命是否对所有人有效?[10]对所有人类有效?对所有的理性存在者有效?很可惜,霍恩屈从了非康德的、但在世界上实践化的普遍化测试,参看,44,47及以下。其缩略形式为“KI-程序”(147以下)[11]。当我能就我自己的人格回答该问题时,我不再需要其他任何人;当他人成为必要时,我就得到了一种陌生的规定(Fremdbestimmung)。“其他所有人”作为审计(Instanz)破坏了自律。康德在他的批判的道德哲学中,既没有认出关于普遍化或一般化的论述,也没有认出依据它们所刻画的程序[12]。他的学说:准则应当能够成为法则,分析性的东西自身便展现为普遍性,反之则并非如此,因为从一般性中得不到任何法则。根据一种普遍化的程序,从KpV中的道德迈向法权论的道路是找不到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在道德哲学中,准则和法则的分阶与法权论中自然状态或私法状态和公共法权的市民状态相对应。过渡是一个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中,这一问题都是从纯粹实践理性中产生出来的,所有人对这种过渡(bei der)的必然接受都处于一种法则性秩序的必然性,不存在任何相反的情况。
“康德的政治哲学”:除过服从自由法则之外,政治还服从假言命令以及明智规则,它们均不从属于《道德形而上学》(MS, AA 06: 217.32-36以下)。
II. 非理想(理念)的规范性
霍恩认为,实践理性产生了两种规范性的变项,理想的和非规范性的。第一种是在GMS和KpV中发展出来的,而第二种是在所谓的政治哲学中产生的,而法权哲学从属于后者。因此,正如霍恩在概要中描述的,非理想性规范是一种较弱的、人类可满足的、依赖情境的规范性变项。截止现在还都挺好。也许当人们思索康德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区别时,人们就能够理解这种区分。更为困难的是,我们在霍恩的著作中找不到一条线索。
霍恩的书是如此架构的,第一章用于处理依赖论和分离论之间的冲突,第二章和第三章处理人权和义务论的法权概念。它们旨在阐明法权关系的普遍奠基。第四章和第五章在“什么使得国家成为理性的命令?”和“政治规范性背景之下的历史哲学”标题之下是共属一体的。第六章是总结章:“作为非理想性规范性理论的康德政治哲学”。第四章和第五章按照它的顺序导向了康德法权论的结构;而历史哲学也是在这儿被引入的,因为它提供了“逃离自然状态”的中介。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过渡的公设是霍恩在内容方面的核心兴趣[13]。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国家的必然性没有与“内在的我的和你的”相勾连,而是奠基在所有外在的、获得的我的和你的的公共法权之上(当然包括内在的我的和你的)?霍恩独具会眼的回答是:在未来公民的临时性占有中,受到规定的土地(Boden?)的唯一性回答了上述问题,在其中,人们碰到了受到规定的国家(203)。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已经通过如下一点得到解决了吗,亦即每个人作为失去财产的居住者处在一处确定的场所之上?诚然,根据自然的或公共公共的法权,临时性的你的和我的属于与法权相关的超越性,但是,这种被规定了的定位(Likalisierung)已经通过内在的我的和你的、以及与之伴随的无可辩驳的、友好的“这里”(Hier)获得了保障。国家秩序所具备的必然性要比霍恩所要求的更多。
在历史哲学中,天意(Vorsehung)的角色(260-264):它对于康德针对每一个国家之严格的忠诚是相当关键,因为如若没有天意之希望的逻辑(这是历史最终所指向的地方),理性禁令即缺少每个人理性的服从(与斯宾诺莎相反)。霍恩的阐释通过霍布斯的指示而得到了补充,后者的理论作为国家奠基的学说仅仅预设了公民可受到伤害的身体,因此,“外在的我的和你的”的组织和配给完全处在利维坦的强力之下(Macht),对洛克和康德而言,它们就处在绝对主义及隐蔽地奴化公民的幽灵之下。在霍布斯那里,公民只是国家的纯然的一部分,每个人都缺乏独立性并被视为君主的御用工具。康德强调,国家的基础若没有一种预先临时的我的和你的就是不可能的(MS, AA 06:312f.),并且,公民若不拥有自己的财产就会是利维坦不自由的工具;如若没有先于国家的临时性的我的和你的,除过自由和平等之外,就不会存在作为公民自律之基础的独立(MS, AA 06: 313‒315)。
霍恩在如下这点上是错误的,亦即根据康德,“法权状态必须被确立为一种强力状态(gewaltsam)”(190);但是,它仅仅吁求一种理性的方式,即当人们能够和平地被联合起来时,每个人能够被强迫进入法权状态,这样会更好。(MS, AA 06: 307 f.; s. a. V-MS/Vigil, AA 27: 516.32 f.:“[……]为了建立法权,法权之前的强力朝向了一种许可法则。”)
MS依赖定言命令,然而,道德和法权的范围并不重合。我们在本书评的第一部分已经看到,作为形而上学的MS在其学说中整合了那些无法从道德的形式原则中无法推导出来的内容。然而,在实定法权中存在如下内容,在责任原则的庇护下,实定法权要求忠诚,尽管它违背了所有的道德。霍恩进一步地引入了一些扬弃了规范性资格的内容,然而,康德把每个人的幸福的实现归入了明智的领域。尤其是这一领域要求一种非理想性的规范。整体上的(gesamt)法权论建立在一种立法的约束性之上,根据这种约束性,法权的可实现性和在政治上必要的、有节制的(gemäßigteren)规范是建立不起来的。
最后,我们将转向如下两点:首先是,先天规范和实定规范之间的冲突,之后是道德规范在幸福实现的领域中所谓的欠缺,后者被归给了非理想性规范。
在冲突情境下的忠诚要求:当伦理学中不朽的公设能够防止绝望时,在对法权的归属中就存在对于由天意引领的历史进步的信任。这种信任可以拯救希望的缺失。“成为一个正直的人(诚实的人)。[……],‘不要把他人看作纯然的手段,要同时将他们视为自在的目的。’”(MS, AA 06: 236.24‒28)[14]如何能够基于道德的基础及其定言命令要求公民不要被看作纯然的手段,然而同时不能放弃忠诚的命令,同时允许军队在恣意地屠杀人类的狂欢时不许反抗?霍恩理应追问,在这种情况下普遍的忠诚义务还有效吗?非理想性规范真的有所帮助吗?绝望依然存在,而这种绝望又被康德的自杀禁令增强了。由于普鲁士的军队的许多自杀对于其余的公民而言与自杀无异,这是与康德的思想相适应的。康德一定依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多得无可奉告。
该书的最后一句是:“康德将所有技艺的善物(Güter )——包括那些被我们看作是道德上的善物——归摄到了幸福的标题之下。因此,按照我们的眼光,他的政治哲学中存在一种严重的、不可修复的弱点。”(341,同见书封)根据霍恩,康德将无法忍受的普鲁士人的幸福问题从理想的规范性中排除了出去,最终从法权中排除了出去;幸运和幸福除过官方的规范之外在康德那里成了可有可无的残渣。在这儿,非理想的规范性发挥着它应有的功能;它有时在道德法则之内有时在道德法则(Gesetzsmoral)之外寻求规范的导向。在康德的理论范围之内,霍恩的说法会变得在“政治哲学”的交界地带有其价值,在理想性的法权规范范围之外,它是以善概念作为引导概念的另一种理论类型,亦即亚里士多德和罗尔斯的融合。因此,霍恩的“非理想性规范”横跨了两种不同的实践哲学范式,一种以法则的概念为依据,一种以善的概念为依据。“非理想性规范”尝试纠正康德式的法则性的,并通过一种定向来补充或代替一种基本的善物。对该理论而言,这是一种赢获吗?或者是向倾向于普遍善好内容的霍布斯主义或父权制的倒退?根据康德,自律的公民(总是:在理念中。)依据形式法则规范自己的行动,以至于每一个人的自由能和其他所有人的自由相协调——正如该法则在内容上规定了行动,支撑着它的伦理上和实用上的远见。因此,在形而上学中加强了的法权中,存在一些重要的预先的规定,通过它,霍恩缺少的东西或许才能够得到填补。因此,形式法则必须担保,每一个人(每一个自然人被赋予积极公民的存在的资格)被规定能够通过劳动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MS, AA 06: 315.21)——针对公民之间的巨大的物质上的不平等的调整工具。另外,康德认为,在其辅助性的历史哲学中,存在一种社会性的力量机制引导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增加。与之相反,霍恩的非理想性的规范拥护另外一种理论类型,它将善置于价值的顶端而代替了康德那里法则所具有的优先性。人们思索一下KpV中的分析论:处于顶端的是定言命令这一自明的事实,之后才引出善和恶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将赞赏这种转向,并去检验,是否法则的原理(Gesetzesprinzip)是否事实上是善的。霍恩是否向通过一种“既-又”(Sowohl-als auch)替换掉“要么-要么”(Entweder-Oder)呢?
总结:尽管有许多可以争论的细节,但霍恩在如下一点上是成功的:霍恩已经使得形式更新了,在其中,我们能够遭遇到作为义务的法权。对于自由人和公民来说,惧怕惩罚是不好的,相反,恰恰是它促发我们去合法权地行动。
Literatur:
Brandt, Reinhard: „Sei ein rechtlicher Mensch!“wie das? In: Sind wir Bürger zweier Welten?
Freiheit und moralische Verantwortung im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 Hrsg. von Mario
Brandhorst, Andree Hahman und Bernd Ludwig. Hamburg 2012, 311‒360.
Cramer, Konrad: Nicht-reine synthetische Urteile a priori. Ein Problem der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Immanuel Kants. Heidelberg 1985.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Jenaer Kritische Schrift en. Hrsg. von Hartmut Buchner und Otto Pöggeler. Hamburg 1968.
Höffe, Otfried: Kants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Eine Philosophie der Freiheit. München
Kant, Immanuel: 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slehre. Hrsg. von Bernd Ludwig.
Hamburg 1998.
Kant, Immanuel: Vorlesung zur Moralphilosophie (Kähler). Hrsg. von Werner Stark. Berlin 2004.
[1] 这个概念是从费里普和墨菲那里接纳过来的,第311页,注释10。
[2] 关于这个问题参看Konrad Cramer关于“不纯粹的先天综合判断”的研究,可惜他没有将此运用到MS中。
[3] 参看,KrV, A 840 ff.
[4] 参看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MAN, AA 04: 467.01‒17)的序言,具体为:康德对外感官对象和内感官的对象,Cramer 1985, 126.
[5] 霍恩指责说,人们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洞见”来承担实定的法权义务的;然而,康德认为,将一般法权秩序的实现同样可被承认为伦理义务。
[6] 黑格尔提出的(舍勒再次承继的)针对康德的形式主义指责,通过MS中的具体的形而上学特征给摧毁了;寄存物在MS中才被迫得以可能,而不是在KpV纯粹形式的层面上;在这一层面它只能被引用,而不能得到辩护。参看,黑格尔《论自然法权的处理方式》,Hegel 1968, 436 u. ö.
[7] S. Kant 1998, 57.
[8] 通过KrV中的模态原理,而模仿“反驳唯心论”,KrV, B 274‒279.
[9] 基本错误的一项根据是,例如和平论著中公共法权的定向;在这儿,现象和物自体的区分还没有专题化,但是,教学库存(Lehrbestand)依赖于直达1797年才展开的私人法权。另外一个点是:非依赖论的作者认为法权仅仅出于臣服的视角,而不是出于立法者的视角,后者已经被敬重为了公民之本体的人格质( die noumenale Personqualität des Bürgers)。
[10] 其他的例证参看,GMS, AA 04: 423; KpV, AA 05: 19, 27. Höffe 2012, 123. 在康德那里,事关人类行动的朴实准则的例证;他对内在的秩序并不感兴趣,而只对法则的测试感兴趣。那些通过测试的法则在主观的意图中依然是准则。建立在可普遍化准则之基础上的“准则伦理学”与其说属于纯粹实践理性的道德性,不如说属于人类学。
[11] 同样贯穿在Höffe 2012中。
[12] 依据所谓的康德70年代后半叶的凯勒伦理学讲座(Moral Kaehler),这一点依然是不确定的,参看康德vgl. Kant 2004, 55‒73.
[13] 还包含如下的观察,作为整体的法权论从属于审判委员会(Urteilstafel),“逃离”(exeundum)标记了道德中三个在内容上被设定了的在法权状态中法权状态必然实现的部分;新的公设(MS, AA 06: 307.08)对应于“一般经验性思维的公设”(KrV, B 265‒294)。布兰特2014,203。这种划分遵从KpV,正如布兰特2014中所明确阐明的那样。
[14] 这一点参见,布兰特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