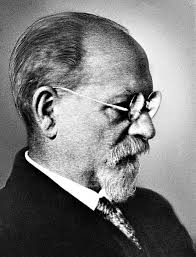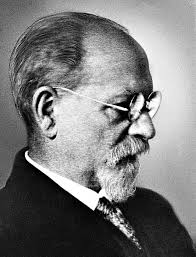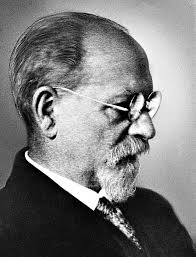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
康德没有真正地展示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

论“实践理性二律背反”的非真实性(非本真性)及其替代方案
就康德论述“二律背反”的状态而言,康德唯独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没有明确地给出正反题(KrV中的四个二律背反、KU中的目的论判断力的背反和MS中经验性占有和理智占有之间的背反)。理由可能有二。一是实践理性中的二律背反的正反题太过明显,没有表述的必要;二是因为明确表述正反题存在困难。
在理论理性中,理念所造成的背反起源于人的认识上的自然倾向,同样,至善的获得起源于“有限理性的意愿”。
Allen Wood认为,至善包含的两种善,亦即道德善和自然善。他将实践理性的对象等同于了“目的”,因此,至善包含着道德目的和自然目的。
康德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的论证依据有:1)实践理性追求无条件者,因此,必然追求至善;2)至善包含德性和幸福两种要素,这二者之间由因果性加以联结。康德认为,道德性规定幸福,在伦理的意义上表现为“应得”。事实上,我们应该对这一二论背反进行细化,这样,我们就可以更为清楚的看到实践理性二律背反的根本内容和含义。
“是”幸福的(尘世中获得幸福)和“应得”幸福。(厘清“规定”的不同含义;澄清真正的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是什么?)
细化1:德性规定幸福,意味着德性就是幸福。这一点之所以不成立,不是因为它自身包含着矛盾,而是因为人的有限性构成了限制。因此,在这里不存在因果性。【在此世获得高级的幸福】
细化2:幸福规定着德性,意味着德性的丧失。因为真正的德性与幸福无关。在这里,因果性也没有发挥作用。
由此看来,在德性与幸福之间,构不成严格意义上的二律背反。 【在此世获得低级的幸福】
根本恶:1)采纳论;2)倾向论。
在第三章中,康德分析了“至上”的双重概念之后,进而将道德律归为一种最高的善,而将德性和幸福构成的完满的善成为“至善”。同样,这种至善的获得仰赖于“综合”的功能,而不是“分析”的功能。
至善在康德体系中的“宗教意义”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说明,但这种充分的说明却又遮蔽了至善概念所引起的“辨证论”所具有的虚假性。这种虚假性主要体现在道德层面,而不是宗教层面。这样一来,使得我们获得一种更为本真意义上的严格伦理意义善的辨证论变得更为困难。
康德对与道德“对象”的说明,是通过两种不同“性质的善”来说明的,它们既不能相互等同,而且不能彼此替换和补充。它们之间的关系无非是,道德善要成为自然善的条件,但这并不能直接表现为对“至善”的直接义务,而是首先是道德义务在先,在其条件下,幸福才会成为义务。但是,这种义务可以从通过第一级序的义务和第二级序的义务得到区分,也就是只有当第一级序的义务得到满足时,第二级序的义务才能成为必要。这样一来,辨证论看来是无从谈起的,而且很容易就被解决了。
但是,康德的解决方案并非如此。【结构掉二律背反或辩证论的辩证意义。1)辩证的意义不清晰;2)即使有辩证,解决起来也是很容易的。】
第三个二律背反:整体之中和整体之外; 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整体之内的两个要素。
之内:抉择的意愿——幸福原则和德性原则。
Beck:至善不是义务;Silber:至善是“范导性责任”。